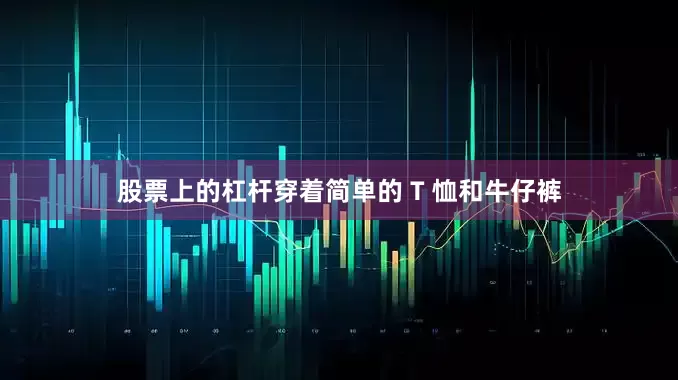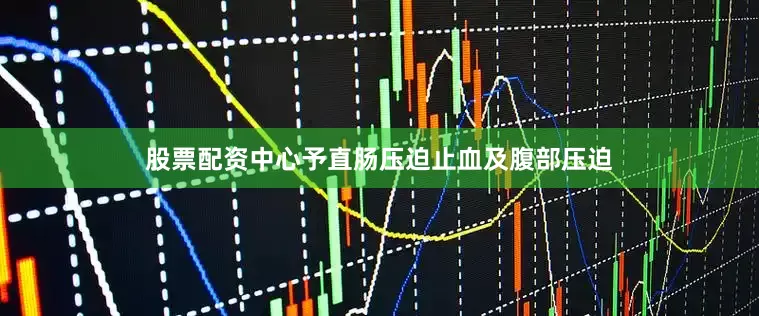咱先从汴京城一个热得能煎鸡蛋的夏天说起。

那天王安石刚从朝堂回来,官服都没来得及换,就蹲在自家后院摆弄他的“试验田”——不是闲得慌,是他琢磨着新的育种方法,非要自己种几棵稻子试试。汗珠子顺着脸颊往下滴,后背的衣服湿了一大片,活像刚从河里捞上来的,手里还攥着个小铲子,跟个老农似的。
“介甫兄!大热天的,你这是跟土地较上劲了?”

老远就听见这大嗓门,王安石抬头一瞧,得,是苏轼。这小子穿得倒凉快,一身月白长衫,手里摇着把折扇,身后小厮还拎着个食盒,里面飘出冰酪的甜香,隔着老远都能闻见。
“你怎么来了?”王安石把铲子往旁边一放,用袖子擦了把汗,语气里带着点无奈。倒不是不欢迎,主要是这俩人凑一块儿,就没安生过——要么为了诗里一个字争得面红耳赤,要么为了新法的事吵到饭都吃不下,活像一对没长大的冤家。
苏轼几步跨进院子,先瞅了瞅那几棵蔫头耷脑的稻子,又看了看王安石的狼狈样,乐了:“我说你这参知政事当得,放着好好的凉房不待,跑到太阳底下晒着,不怕中暑?”
“少贫嘴。”王安石白了他一眼,“你拎着食盒过来,不是专门来笑话我的吧?”
“哪儿能啊!”苏轼把食盒往石桌上一放,打开盖子,里面是冰镇的杏仁酪,还冒着凉气,“知道你忙新法的事,肯定没顾上吃点心,特意让家里厨子做的,快尝尝!”

王安石也没客气,俩人就坐在树荫下吃了起来。冰酪入口凉丝丝的,刚压下去点暑气,苏轼就开口了:“介甫兄,你那青苗法,我还是觉得不对劲。前几天我去乡下,见着有农户为了还青苗钱,把家里仅有的几亩地都卖了,这哪是帮百姓,分明是坑百姓啊!”
这话一出口,王安石手里的勺子顿了顿。他知道苏轼直性子,有啥说啥,但这话还是戳到了他的痛处。“子瞻,”他放下勺子,语气沉了点,“新法推行哪有一帆风顺的?地方官把好事办坏了,贪赃枉法,这能怪新法本身?我在京城听奏报,还有农户靠青苗钱种活了庄稼,娶上媳妇的呢!”
“那是少数!”苏轼也来了劲,把扇子往石桌上一拍,“我走了三个县,十个农户里有六个都在愁还不上钱,你说这是少数?你就是太固执,总觉得自己想的都对,听不进别人的劝!”
“我固执?”王安石也火了,声音提高了八度,“我推行新法,是为了让朝廷有钱,让百姓不挨饿,不是为了我自己!你倒好,天天在朝堂上跟我对着干,还写文章讽刺新法,你这是为百姓好,还是为了逞口舌之快?”
俩人越吵越凶,树上的知了都不叫了,管家在旁边急得直搓手——这两位都是朝廷重臣,一个是参知政事,一个是翰林学士,真要是吵急了,他这小管家可担待不起。
就在这时,苏轼突然“噗嗤”一声笑了。
王安石正说得激动,见他笑了,愣了:“你笑啥?”

苏轼指了指王安石的下巴,忍着笑:“介甫兄,你下巴上沾了杏仁酪,活像个偷吃东西的小孩,还在这儿跟我较真呢!”
王安石一愣,伸手摸了摸下巴,还真摸到了甜腻的残渣。他也忍不住笑了,刚才的火气一下子消了大半:“你这小子,就会转移话题。”
“不是转移话题,”苏轼拿起食盒里的手帕,递给他,“咱今天不说朝政,就说点别的。我昨天写了首新词,念给你听听?”
王安石点点头,苏轼清了清嗓子,念了起来:“大江东去,浪淘尽,千古风流人物……”
刚念到一半,王安石突然打断他:“‘浪淘尽’这句,力道不够。”
苏轼脸一垮:“怎么又不够了?我觉得挺有气势的啊!”
“‘淘尽’太柔了,”王安石端起旁边的凉茶喝了一口,慢悠悠地说,“不如改成‘浪淘空’,‘空’字更有劲儿,把那些风流人物的消散写透了,你琢磨琢磨?”

苏轼皱着眉想了想,眼睛一下子亮了:“哎,还真别说,改了之后,那股子豪迈劲儿更足了!介甫兄,你这脑子是怎么长的?刚才还跟我吵得脸红脖子粗,这会儿又帮我改词了。”
王安石哼了一声:“我是就事论事,跟你吵归吵,好句子还是要认的。”
俩人就这么你一句我一句,从诗词聊到美食,从天气聊到民生,太阳快落山了都没发觉。等苏轼要走的时候,王安石还特意把自己培育的新稻种抓了一把,塞给他:“带回你家院子试试,说不定能长出好谷子。”
苏轼接过稻种,揣在怀里,挥挥手:“行!等长出谷子,我第一时间送过来给你尝!”
可谁也没想到,这看似平常的一次见面,没过多久就出了大岔子。
那年秋天,苏轼因为写了篇《湖州谢上表》,里面有句“愚不适时,难以追陪新进”,被人告到了宋神宗那儿,说他讽刺新法,诋毁朝廷。这就是后来闹得沸沸扬扬的“乌台诗案”。
消息传到王安石耳朵里的时候,他正在书房批改新法的奏报。手里的笔“啪嗒”一声掉在纸上,墨水晕开一大片。他赶紧让人备车,往皇宫赶——苏轼这小子,就是嘴欠,写文章总爱带点刺,这下好了,让人抓住把柄了!
到了皇宫,王安石直接求见宋神宗。神宗见他来了,也知道他是为了苏轼的事。“介甫,你是来为苏轼求情的?”
王安石点点头,语气诚恳:“陛下,苏轼虽然说话直,写文章爱带点讽刺,但他的心是好的,绝没有诋毁朝廷的意思。要是因为这点小事就治他的罪,不仅会寒了天下文人的心,还会让人觉得陛下容不下不同的声音啊!”
神宗皱着眉,没说话。他也知道苏轼有才,可这次告苏轼的人太多,证据也“确凿”,不处理确实不好交代。
王安石见神宗犹豫,又补了一句:“陛下,当年太宗皇帝广纳贤才,不管是赞成朝廷政策的,还是反对的,只要有才华,都能得到重用。苏轼是难得的人才,要是杀了他,那真是朝廷的损失!”
神宗想了半天,终于点了点头:“好吧,看在你的面子上,不杀他,贬到黄州去,让他好好反省反省。”
王安石松了口气,连忙谢恩。他知道,能保住苏轼的命,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。
消息传到苏轼耳朵里的时候,他正在大牢里待着,以为自己这次肯定活不成了。听说被贬到黄州,还愣了半天,后来才知道是王安石帮他求的情。他心里又感动又愧疚——自己总跟王安石吵架,还写文章讽刺他的新法,可在自己危难的时候,却是王安石站出来帮了他。
苏轼被贬到黄州那天,王安石没去送他,只让人给了他一封信,里面就一句话:“到了黄州,好好吃饭,好好写文章,别再惹事。”
苏轼看着信,笑了,眼眶却有点红。他把信收好,带着家人,往黄州去了。

在黄州的日子,苏轼倒安分了不少。他在城东开垦了一块地,自己种庄稼,还给自己取了个外号叫“东坡居士”。没事的时候就写写诗、做做词,偶尔还跟当地的农夫聊天,日子过得也算惬意。他写的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《赤壁赋》,都是在这个时候写出来的。
而王安石呢,没过多久就因为新法推行不顺,辞了官,回了江宁老家。他在老家盖了个小院子,种了很多花,每天看看书、种种花,偶尔也会想起苏轼——不知道那小子在黄州过得怎么样,有没有再惹事。
一晃四年过去,苏轼被调回了京城。他一回来,没先回家,直接去了江宁拜访王安石。

那天天气特别好,王安石正在院子里浇花,见苏轼来了,又惊又喜:“你怎么来了?”
“来看看你啊,介甫兄!”苏轼还是老样子,大大咧咧的,“我在黄州的时候,总想起你当年帮我的事,这次回来,第一时间就来谢你。”
王安石摆摆手:“谢什么,都是过去的事了。你在黄州过得怎么样?我听说你还种了地,成了‘东坡居士’?”
“别提了,”苏轼笑着说,“刚开始种地的时候,还把庄稼种死了不少,后来慢慢摸索,才种活了。不过也挺好,天天跟土地打交道,心里踏实。”
俩人又像以前一样,坐在院子里,喝着茶,聊着天。这次没聊朝政,只聊诗词、聊民生、聊这些年各自的经历。苏轼拿出自己在黄州写的词,念给王安石听。王安石听着,时不时点头:“不错不错,比以前成熟多了,黄州的日子没白过。”
“那是,”苏轼得意地说,“不过还是比不上你,你要是还在朝堂,肯定能写出更好的文章。”
王安石笑了:“我现在这样挺好,不用管朝堂上的事,天天种种花、看看书,比以前轻松多了。”

太阳快落山的时候,苏轼要走了。他看着王安石,认真地说:“介甫兄,以前我总跟你吵架,还说了你不少坏话,你别往心里去。”
王安石拍了拍他的肩膀:“都是为了朝廷,为了百姓,有什么好往心里去的?再说了,要是没有你跟我吵架,我可能还不知道自己的新法有那么多问题呢!”
苏轼笑了,王安石也笑了。夕阳照在俩人身上,把影子拉得长长的,像一对老朋友,又像一对“老冤家”。
可好日子没过多久,苏轼又出事了。
这次是因为他在京城写了几首诗,里面有句“根到九泉无曲处,世间惟有蛰龙知”,又被人告了,说他把自己比作“蛰龙”,不把皇帝放在眼里。神宗虽然没治他的罪,但也把他贬到了杭州。
苏轼离京那天,王安石特意去送了他。俩人在城外的茶寮坐了一会儿,王安石给了他一包江宁的新茶:“到了杭州,好好做事,别再写那些容易让人挑刺的诗了。”
苏轼接过茶,点点头:“我知道了,介甫兄。你在江宁也要好好照顾自己,多注意身体。”
这次分别后,俩人就很少见面了。苏轼后来又被贬到惠州、儋州,一路向南,离京城越来越远;而王安石则在江宁老家安度晚年,偶尔会听说苏轼的消息,知道他在贬谪之地也没闲着,要么修水利,要么办学堂,心里还挺欣慰。
元祐元年,宋哲宗即位,司马光被重用,新法被全部废除。消息传到江宁,王安石心里很不是滋味,他知道自己一辈子的心血就这样没了,但也没多说什么,只是每天坐在院子里,看着自己种的花,沉默良久。
没过多久,苏轼被调回京城,担任翰林学士。他回京城后,第一件事就是去江宁看望王安石,可没想到,刚到江宁,就听说王安石病了。
苏轼赶紧去了王安石的住处,见他躺在床上,脸色苍白,比以前瘦了不少,心里很不是滋味。“介甫兄,你怎么把自己搞成这样了?”
王安石笑了笑,声音很轻:“老了,身体不行了。你能来看我,我很高兴。”
俩人聊了很久,从新法聊到往事,从诗词聊到人生。苏轼说:“介甫兄,其实我后来想通了,你的新法,有些确实是为了百姓好,只是推行的时候出了问题。”
王安石点点头:“我知道,当年我太急了,没考虑到地方的实际情况,才把好事办坏了。”
那天,苏轼在王安石家里待了很久,直到天黑才离开。他走的时候,王安石还特意让家人把自己珍藏的一本《诗经》送给了他:“这本书陪了我很多年,现在送给你,希望你能好好保管。”
苏轼接过书,郑重地点点头:“我会的,介甫兄。你好好养病,我还会来看你的。”
可苏轼没等到下次见面的机会。元祐元年四月,王安石在江宁去世,享年六十六岁。
消息传到京城,苏轼正在书房写文章,手里的笔一下子掉在地上。他愣了很久,才反应过来,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。他想起俩人以前吵架的样子,想起王安石帮他求情的样子,想起在江宁院子里聊天的样子,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,难受得不行。
后来,苏轼主动向朝廷请求,为王安石撰写墓志铭。他在墓志铭里写道:“介甫先生,学贯天人,才高八斗,虽与吾政见不同,然其心为公,其志为民,吾深敬之。”
这篇墓志铭,成了俩人一生友谊的最好见证。他们是政见不同的“冤家”,也是惺惺相惜的朋友;他们吵过、闹过、互相讽刺过,但在危难时刻,却总能为对方伸出援手。
苏轼后来在回忆王安石的时候,曾说过这样一句话:“介甫兄虽然固执,但他是个好人,是个为百姓着想的好官。我这辈子,能有这样一个‘冤家’朋友,是我的幸运。”
是啊,人生在世,能遇到一个既能跟你吵得面红耳赤,又能在你危难时挺身而出的朋友,确实是幸运。王安石和苏轼的故事,就像大宋历史上的一束光,照亮了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,也让我们看到,真正的友谊,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,而是在吵吵闹闹中,越来越深厚,越来越珍贵。
互动环节
聊完王安石和苏轼这对“冤家”的起起落落,是不是觉得这俩大宋大佬特别真实?没有一点官员的架子,吵起架来像小孩,帮起忙来又特别仗义!其实历史上还有很多这样有血有肉的人物,比如李白和杜甫的“诗坛知己”,比如李清照和赵明诚的“文艺夫妻”。你还想知道哪对历史人物的故事?评论区告诉我,下次咱们就扒一扒他们的人生趣事!
信康配资-网上正规实盘配资网站-配资炒股开户网站-实盘杠杆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- 上一篇:低息配资开户观察、解读与分析系列第140期
- 下一篇:没有了